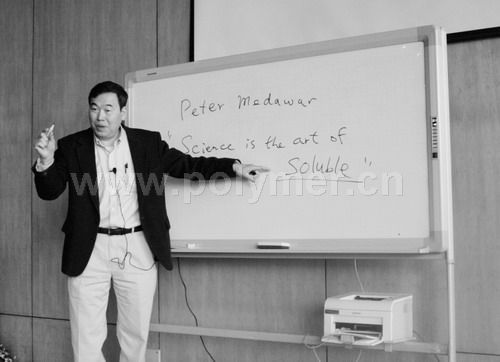

魂牽夢縈:還多年的心愿
蒲慕明是美籍華裔科學家,但他卻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。這位美國科學院院士、中國科學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首任和現任所長,多年來一直兢兢業業、孜孜以求,對中國科學的發展,做了最真誠、最實質、也是最為具體的工作。
大陸出生,臺灣長大,美國留學,又回到中國來,這是蒲慕明的特殊經歷,他不管在什么地方,始終對中華民族的狀況深深關切,而且如果能夠做一點事情就盡量去做,在兩岸三地用自己力量促進交流,加深彼此的理解。
“打從年輕時代起,我就有比較關心社會的傾向。我走到今天的這一步,也是自然而然的。”蒲慕明說。
蒲慕明1948年在南京出生。還在襁褓之中,他便隨父母遠渡臺灣。
蒲慕明的父親蒲良梢先生,1938年畢業于上海交大,是機械系航空工程組的第一屆畢業生。那一屆的畢業生全部投筆從戎,加入抗戰成為空軍后勤人員。后來國民黨政府要造飛機,蒲良梢不久便被派往美國,學習螺旋槳發動機制造技術,他學成回國之后,成為南京發動機制造廠的第一批技術人員。
1949年,母親帶著蒲慕明和他的姐姐,從南京的下關乘船到武漢,然后到了廣州,再從廣州坐船到臺灣。當時被母親抱在懷中的蒲慕明還沒有記憶。但蒲慕明在后來知道,中國航空工業的先驅們大多都是父親的同學,而父親的畢生志愿,就是想制造出一架中國自己的飛機。
蒲良梢先生60多歲時,任臺灣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,終于造出了“經國號”飛機。蒲良梢先生退休之后,在其事業的最后10年里再創輝煌,在逢甲大學創辦了臺灣最好的航空工程系。“父親的人生經歷對我的影響很大,他的一些好朋友都成為我的師長。”蒲慕明對本報記者回憶。
蒲慕明家中的墻上掛著一幅詩作:“忘卻離鄉今幾年,水隔青山天外天,舊時歡笑渾為夢,新來思緒總難眠。海外飛傳無限意,天涯相贈有詩篇,相知一世知何事,長留肝膽照人間。”這是蒲慕明的父親與其同學、曾任鐵道部總工程師的鄒孝標的唱和之作。父親作詩,由鄒孝標書寫,時空阻隔不了父輩歸根的心愿。
1999年回到中國大陸, 年逾50歲的蒲慕明已經是世界知名科學家,他最重要的是還一個心愿。
因為蒲慕明決定到上海工作的緣故,蒲慕明的父親也希望來上海常住,不幸的是,2000年的冬天老人家從浦東機場到市區路上遭到車禍,他所乘坐的出租車被一輛環保卡車沖撞,造成頭部、肺部、眼睛多處挫傷,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。因為這次車禍,此后老人家一直伴有失眠、哮喘、失明、行動不便等,身體就此每況愈下。
蒲慕明父親遭受的車禍,其實是開卡車的那位肇事環保工人的全責。
但老人家在住院治療期間,當工人帶著一串香蕉去看望他,老人家自己反而過意不去。因為手頭沒有現金支付,老人家就向來探視的王燕借了50元錢,感嘆地對王燕說:這位工人給我送來了香蕉,冬天里的香蕉很貴,他的妻子已經下崗,小孩還在上學,他的家很窮困、真是很不容易吶!等那位工人下次再來醫院看望,老人家當即就給了這位工人50元作為補償。后來,老人家又給了那位工人100元錢。
2007年12月5日,接到父親不幸在美國去世的噩秏,紅著兩眼的蒲慕明早上一走進辦公室,就對王燕哽咽地說:我的父親已過世了。王燕說:那您就趕緊回家料理喪事吧。蒲慕明卻說:不用了,即便是我現在就回去,也已經見不到他的最后一面,還是把我在上海的工作忙完再說吧!
一個小時之后,處理好當日電子郵件的蒲慕明從辦公室出來,又鄭重其事地對王燕說:父親逝世純屬我的私事,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,更不要影響研究所的正常工作。
但是蒲慕明內心一直存有遺憾:當父親去世時,自己不能守候陪伴在身邊,給父親以些許的慰藉。蒲慕明只記得自己小時候,有一次父親送他去上學,而后在霞光中匆匆離去的背影。那正像是自己少時熟讀過的、朱自清先生寫他父親的《背影》。
- 相關新聞
- 無相關新聞